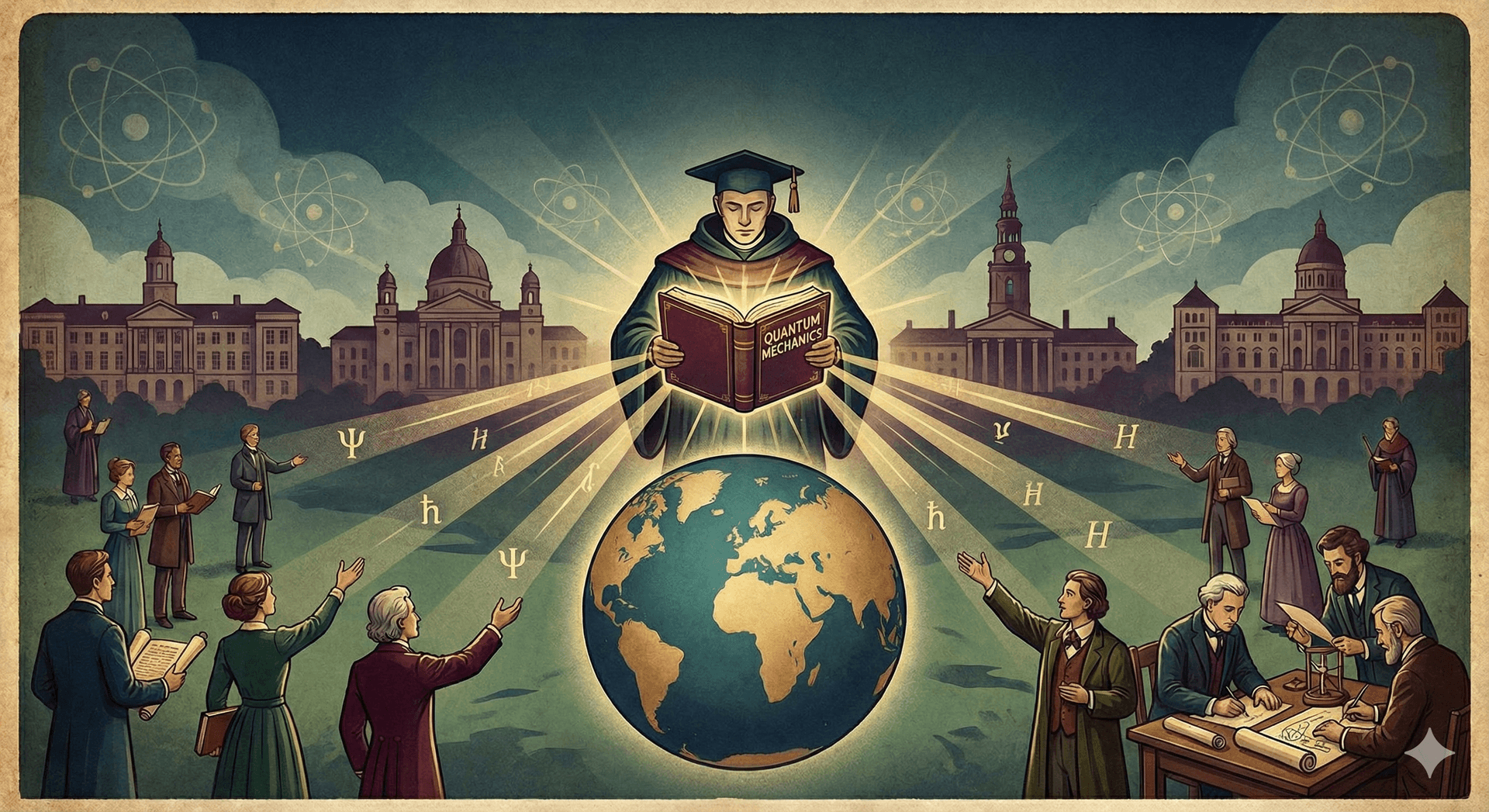
今年是量子力學問世百周年慶,隨著各種慶祝活動逐漸接近尾聲,筆者想要來談談一個比較少人談論的主題,就是量子力學這樣一個匪夷所思的新思潮是如何傳播開來的。雖說上世紀的二零年代不像今天網路世界那樣方便,但是比起過去靠口語相傳,或是藉著手抄本來傳播的時代,那還是不可同日而語。當時量子力學的論文都刊載在著名的德文期刊或英文期刊,當時世界許多地方的大學圖書館都有收藏這些期刊。但是熟悉量子物理發展的讀者們都知道,光看這些文獻如墮五里霧中,需要解說的脈絡太多了,因為量子物理是複雜的數學理論與龐雜的光譜實驗數據交纏所產生的詭異產物,與傳統的古典物理的差異大到連許多老一輩的傑出物理學家都不願接受,所以當時對量子力學好奇的年輕學生要憑著一己聰明才智,從期刊文章裡學會正確的量子力學,應該是一件非常高難度的挑戰。
那麼量子力學是怎麼在全世界各個角落發芽進而開花結實的呢? 這個過程其實與當年佛教東傳,或是基督教的使徒們向萬邦傳送福音的過程,還真是有許多類似的地方。我們會發現,如同當年的高僧或使徒一般,量子力學一開始的傳播也非常仰賴極少數的關鍵人物,這些人帶著極高的熱忱與極優異的才能,逐漸將量子力學的種子撒在年輕一代學者的腦海中。
當然我們也知道當年使徒傳教的過程血淚斑斑,常遭到周遭政府的彈壓,為首的使徒幾乎全數殉教,而佛法傳播的時候,佛門弟子也屢遭外道的攻擊,甚至連號稱「神通第一」的目犍蓮都遭到殺身之禍。無獨有偶的是量子問世的時代正是整個世界剛結束一場極為血腥的大戰,而又慢慢走上下一場更加血腥的大戰的道路上,所以許多人在傳播的過程中遭受到許多的人生波折,甚至被捲進戰爭的漩渦之中,這使得量子力學的傳播過程中添上了一抹悲壯的色彩。
這些挑起將新思潮帶到各地的人物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與幾個當時量子物理的重鎮都有非常深厚的緣分。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有波爾坐鎮的哥本哈根研究所,有波恩掌舵的哥廷根大學,還有索末菲主持的慕尼黑大學。其他像是由史特恩負責的漢堡大學,由埃倫費斯特掌旗的萊頓大學,或是愛因斯坦的母校,位於瑞士蘇黎世的聯邦理工學院,最後還要算上量子物理的兩員大將,普朗克與愛因斯坦所在的威廉皇帝研究所,都是培養新世代的量子力學學者的重要機構。這與宗教傳播中講究師承衣缽有幾分相似,不過物理終究是講求客觀的自然科學,不至於在師承衣缽這回事過分堅持就是了。以下我們就針對幾個有代表性的國家,追溯一下量子力學是如何被引入傳開的。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與歐洲向來關係緊密的美國。在二十世紀初,美國的理論物理並沒有受到太多重視,著名的統計物理大師,吉布斯,當年在耶魯大學,可謂一支獨秀,但也是非常孤單。到了所謂的舊量子論發展的階段,美國其實有一些零星的貢獻,主要是來自哈佛的肯布爾(Edwin Crawford Kemble 1889 –1984),他在1919年開始在哈佛任教。他的頭一個弟子,凡累克(John Van Vleck)與肯布爾曾經試圖在波爾模型引入立體的電子軌道來解釋氦原子光譜,可惜沒有成功。肯布爾教過的另一位學生斯拉特(John Clarke Slater, 1900– 1976) 曾經與波爾,克拉默斯一起提出著名的BKS理論。凡累克還曾在1924年發表過一篇討論色散與吸收的文章。但是不論是凡累克,還是斯拉特,在量子力學問世時,都處在相對孤立的學術環境中。反倒是人在歐洲的拉比與歐本海默,在量子力學引入美國這件事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這一期雙月刊特地將拉比的回憶翻譯與各位讀者分享,可以讓大家感受到當時美國科學家在歐洲同行眼中是如何地被邊緣了。相形之下,彼時尚在哥廷根求學的歐本海默,就顯得鶴立雞群,相當地突出了。拜前幾年上映的電影「歐本海默」之賜,新世代的讀者認識這位曼哈頓計畫總主持人的比例大幅提升,但是電影對於他在哥廷根時代著墨不多,對於他在引量子力學進美國的影響力,更是隻字未提,所以讓筆者稍作補充。
歐本海默在1926年到德國哥廷根大學,在馬克斯·波恩指導下求學。當時波恩與海森堡、丹剛建立了矩陣力學,而相關的人物如包立、狄拉克、來自義大利的費米和來自匈牙利的愛德華·泰勒都在哥廷根校園內出沒,而且歐本海默很高調,與保守矜持的歐洲學生的行為舉止截然不同。他在研討會上常常放言高論,甚至還會跳上講台,寫起黑板來說明他的見解。這種喧賓奪主的行為讓波恩其他學生非常不爽,以致以瑪麗亞-格佩特為首,眾人向波恩提交了一份多人聯署的請願書,他們宣稱要是波恩不再約束歐本海默的行為,他們就要杯葛波恩的課! 老練的波恩只將請願書放在歐本海默能看到的桌上,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歐本海默也不單單只是個愛現的美國佬。在哥廷根期間,歐本海默發表了十幾篇論文。他在1926年發表的第一篇論文是關於分子頻譜的量子理論。他發明出一種計算能階躍遷機率的方法,並將其應用於用X光撞擊氫發出電子的光電效應現象,算出K緣的吸收係數。他和波恩發表的影響最大的一篇論文是有關分子的數學描述。他主張把原子核的運動與電子的運動分開處理,進而簡化計算的方法,這個方法後來被稱為「波恩-歐本海默近似法」。這篇論文成為他物理生涯中被引用最多次的論文之一。當他在1927年3月通過博士口試後,擔任口試委員的「哥廷根雙璧」之一的詹姆士·法蘭克教授鬆了一口氣,他打趣地說:「終於結束了。要不然都快換他來給我口試了。」
歐本海默拿到學位後,在1927至1928學年度間,上半學年在哈佛,下半學年則在加州理工學院。他在加州理工時結識了化學家萊納斯·鮑林,兩人一同研究化學鍵的本質。這本來是一段佳話,但是兩人的合作後來卻因歐本海默企圖引誘鮑林的妻子艾娃·海倫·鮑林到墨西哥去幽會而戛然而止。因為艾娃·海倫不但拒絕了歐本海默,還把這件事告訴鮑林,歐本海默和鮑林之間的友誼也就煙消雲散了。因為歐本海默荒唐行徑而交惡的鮑林,其實也算是將量子力學引進美國的一個要角。鮑林原先在加州理工學院,師從羅斯科·迪金森和理查德·托爾曼,研究利用X射線繞射技術測定晶體結構。1925年,他以最優等成績獲得物理化學和數學物理博士學位。 隔年,鮑林獲得古根漢獎學金前往歐洲四處學習,他先後師從索末菲、波爾和薛丁格等人。約莫就在此時,鮑林開始對如何將量子力學應用於原子和分子的電子結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蘇黎世,鮑林也接觸了沃爾特·海特勒和弗里茨·倫敦對氫分子鍵合的早期量子力學分析。 鮑林將他歐洲之行的兩年時間都投入到這項工作中。他成為量子化學領域的先驅科學家之一,也是將量子理論應用於分子結構的先驅。 1927年,鮑林回到美國,在加州理工學院擔任理論化學助理教授。 他在加州理工開設的第一門課程就是「波動力學及其在化學上的應用」。後來他將這門課的講義整理成文,於1935年出版了《量子力學導論——及其在化學中的應用》,這是歷史上第一本以化學家為對象的量子力學教科書。鮑林後來於1954年因在化學鍵方面的工作取得諾貝爾化學獎。1963年因反對核彈在地面測試的行動獲得1962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與諾貝爾獎無緣的歐本海默應該很羨慕他吧?
1928年秋,歐本海默訪問荷蘭萊頓大學的研究所,在那裡他居然以荷蘭語講課,讓人印象深刻。離開萊頓後,他又到了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參與包立對量子力學和連續光譜的研究。雖然包立只比歐本海默大四歲,歐本海默終生都十分敬重包立。歐本海默是少數擠進量子力學狹小舞台上的美國人,這讓他擁有量子力學的第一手研究經驗,這也讓他對量子力學的知識遠比閱讀當時期刊上的論文更深入,也更實用。回到美國後,歐本海默應邀到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當副教授。他因學識精湛,興趣廣博,贏得了不少物理學家的青睞。後來搬來美國的德裔物理大師,漢斯·貝特對他的評價是這樣子的:
“他的教學風格中最重要的,莫過於他非凡的品味。從他親手所選的課題可以看出,他時時刻刻都認識到哪些才是重要的問題。他真的和這些問題朝暮相處,盡心尋找答案,並把自己的各種顧慮表達給整個團隊。”
漢斯·貝特也頗為贊賞歐本海默的領導才能:
“(歐本海默的)研究團隊最興旺之時,有八到十個研究生和六個左右的博士後。他每日一次在辦公室和他們開會,一個一個地詢問他們各自研究課題的進展。他對一切都感興趣,可以在一個下午把電動力學、宇宙射線、電子成對產生和核物理都一一討論。”
歐本海默十分自負,個性也算不上親切,但是對當時的美國學生卻頗具吸引力。他喜歡用極其複雜卻又十分優雅的數學方法來證明物理原理,所以歐本海默的論文也十分難懂。但他往往會因為性急而犯下數學錯誤。他的學生史奈德曾經說過:「他的物理很好,算術卻很糟糕。」這一點倒是與他的恩師,波恩有幾分相似,不過波恩人品溫厚,與歐本海默不同。歐本海默的學生們後來成了美國理論物理的中堅,他的學生也傳承了他的風格。其中成就最大的當屬量子電動力學大師許文格,兩人相處時間雖不長,但是歐本海默對許文格的影響卻相當深遠,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參照筆者寫的「孤高的物理學家:許文格 (一) 晝伏夜出的天才」一文。二戰爆發之後,大批歐洲的科學家流亡來到美國,其中不乏在量子力學發展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優秀學者,他們在美國眾多大學傳授量子理論,讓美國在戰後執世界物理界之牛耳,但是這些成就還是建立在歐本海默,拉比以及鮑林等人奠定的基礎上,他們還是功不可沒。
相較於隔著一個大西洋的美國,也許你會以為緊鄰德國的波蘭應該很快就趕上量子的浪潮,其實不然。當量子力學問世之時,波蘭才剛復國不到十年,而且當時波蘭的第二共和國深受內憂外患之苦,所以量子力學意外地要等到二戰之後才由多位波蘭科學家引進而逐漸在波蘭生根。其中最有影響力的當數沃伊切赫·西爾維斯特·彼得·魯賓諾維奇(Wojciech Rubinowicz,1889-1974),利奧波德·英費爾德(Leopold Infeld,1898—1968),揚·魏森霍夫(Jan Weyssenhoff, 1889-1967)與揚‧布拉頓(Jan Antoni Blaton 1907 - 1948 ) 等四人。他們的人生可說是南轅北轍,唯一的共同點只有都曾在德國或是瑞士求學過這一點。
讓我們先從最年長的魯賓諾維奇開始吧。他出生於奧匈帝國布科維納的薩達戈拉,父親曾參加1863年的波蘭一月起義。 魯賓諾維奇於1908年進入切爾諾維茨大學學習,並於1914年獲得博士學位。 (切爾諾維茨大學在當時的正式名稱是Franz-Josephs-Universität ,它是奧匈帝國在1875年創立的大學,切爾諾維茨在一戰後成為羅馬尼亞的領土,1940年被蘇聯佔領成為烏克蘭的領土)。1916年,他前往慕尼黑大學,師從索末菲,後來還成為索末菲的助手。在慕尼黑期間,魯賓諾維奇發表了關於索末菲三大主要研究方向的論文,這三大方向分別是:索末菲對波爾原子理論的擴展、數學物理以及繞射理論;魯賓諾維奇畢生都致力於這些領域的研究。他後來出版了《索末菲多項式方法》中描述了用多項式方法求解量子力學特徵值問題的工作,並在《克希荷夫繞射理論中的繞射波》中發表了關於繞射理論的研究成果。魯賓諾維奇在量子理論領域的第一個成就是發現了原子光譜裡的躍遷選擇定則,並在1918年發表了相關成果。他在1918年成為切爾諾維茨大學的特聘講師。一次大戰之後切爾諾維茨變成羅馬尼亞的領土,所以他去哥本哈根波爾研究所待了一年,之後受聘於南斯拉夫的盧布爾雅那大學,在那裡擔任教授。
1922年,他成為利維夫(Lviv)理工學院的教授。 (利維夫始建於1256年,曾為加利西亞-沃里尼亞王國的首都,1349年被併入波蘭,1772年,伴隨著瓜分波蘭的狂潮,利維夫改隸屬奧地利,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短命的西烏克蘭人民共和國也以這裡為統治中心,之後,這座城市再度回歸波蘭。1939年德蘇聯合入侵波蘭以後,利維夫再度成為蘇聯的烏克蘭共和國的領土。)他在利維夫的時候,最重要的成就是關於天文學家發現的新譜線。未來的威爾遜山天文台台長艾拉·S·鮑文(Ira Sprague Bowen,1898—1973)在1928年主張過去在宇宙星雲中發現了一些譜線,並不是新元素的光譜,而是雙電離氧O2+的譜線,他稱之為“禁線”,因為它們違背當時認定的選擇定則,這引起了轟動。同年,魯賓諾維奇成功證明,這些譜線的起源機制與通常觀測到的譜線完全不同,它們遵循不同的選擇定則。這些譜線不符合標準電偶極子(E1)選擇規則,但允許作為磁偶極(M1)或電四極(E2)躍遷。他進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譜線理論,並提出用北極光的綠色譜線來驗證他的理論。根據他的論文,美國對這條光譜線進行的實驗,以及在阿姆斯特丹彼得·季曼實驗室對其他光譜線進行的實驗,都證明了他的理論是正確的。這個理論對後來卡斯特勒(Alfred Kastler )發明光學幫浦的助益極大。卡斯特勒在獲得諾貝爾獎後表示,魯賓諾維奇的研究對他的光學幫浦發現做出了貢獻。 1969年魯賓諾維奇80歲生日之際,卡斯特勒為他寫了一首打油詩來賀壽呢。
1937年至1941年間,魯賓諾維奇跳槽到利維夫的約翰·卡西米爾大學當物理系系主任。利維夫先是被蘇聯佔領,後來又被納粹佔領。在納粹佔領利維夫時期(1941年至1944年),他必須秘密授課。二戰後利維夫被劃成蘇聯領土,魯賓諾維奇在華沙大學擔任理論物理學教授,直至1960年。他在戰後培養眾多波蘭的理論物理學家,尤其是他寫了許多膾炙人口的教科書,對波蘭物理界影響深遠。
除了魯賓諾維奇之外,另外一位重要的推手是利奧波德·英費爾德(Leopold Infeld)。他出生於克拉科夫的波蘭猶太家庭,當時克拉科夫是奧匈帝國的一部分,1918年被併入獨立的波蘭。他最初在一所猶太宗教學校接受教育,之後進入一所中學就讀。 1916年,他以優異的成績高中畢業。作為奧匈帝國公民,他應徵入伍,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退伍後,他進入克拉科夫的雅蓋隆大學(哥白尼的母校)學習物理。後來他進入柏林大學就讀。 1921年,他獲得博士學位。 他的猶太血統,讓他遇到了重重阻礙。 所以他在畢業後一路在求職路上跌跌撞撞。博士畢業後九年,他才終於在利維夫的揚·卡齊米日大學理論物理系取得教職。 1932年,他在萊比錫的訪問期間寫了兩篇論文,標誌著他國際學術生涯的開端:第一篇論文是與荷蘭數學家范德瓦爾登(van der Waerden)合著的論文,他們將所謂的旋量演算發展成適用於廣義相對論的形式(范德瓦爾登先前已將旋量演算引入狹義相對論)。在第二篇論文中,英費爾德在廣義相對論的時空中找到了狄拉克方程式的一種形式。
英費爾德科學生涯的下一個階段是作為洛克菲勒基金會學者在英國劍橋大學進行為期兩年的訪問(1933-1935年)。 在那裡,他結識了流亡到英國的馬克斯‧波恩。他們的合作成果是所謂的波恩-英費爾德電動力學,這是一種對馬克士威的古典電動力學的推廣,使其能夠對電磁場進行非線性描述。這個理論是通往量子電動力學道路上的一個過渡產物。
1936年,英費爾德申請維爾紐斯大學教授職位被拒絕後決心離開歐洲,他到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員,並開始與愛因斯坦合作。 這次合作促成了關於廣義相對論運動方程式,即所謂的愛因斯坦-英費爾德-霍夫曼理論。在普林斯頓的兩年裡,英費爾德與愛因斯坦合作寫了《物理學的演化》一書。該書成為國際暢銷書,自出版後的七十年間,版本超過200版。1938年,他成為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物理學教授。這段時期,他的論文主要集中在相對論宇宙學和因子分解理論(一種解決特徵值問題的方法)。與留在故鄉的其他波蘭科學家相比,他免遭戰亂之苦,似乎幸運許多,但是戰後他被誣告與波蘭共產黨有聯繫,並可能向他們出售涉及核武的軍事機密。由於不願失去在加拿大的職位,再加上他對二戰後完全依賴蘇聯的波蘭的共產主義新政權的實況一無所知,英費爾德最初試圖透過從多倫多大學請假前往波蘭工作,但遭到加拿大校方拒絕。不但如此,他還被加拿大剝奪了公民身份,甚至被宣佈為叛國者。要等到 1995年,多倫多大學才追授他榮譽退休教授稱號,洗刷他的冤屈。只是英費爾德個人的不幸反倒促成了量子力學在波蘭的發展。1950年,他擔任華沙大學理論物理學教席。他與魯賓諾維奇共同創立了華沙大學理論物理研究所。 1953年,他開始在波蘭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工作。英費爾德的博士生中後來出現許多後來成為頗具影響力的理論物理學家。
除了魯比諾維奇與英費爾德之外,還有兩位從國外回來的物理學家對引進量子力學到波蘭也頗有建樹,他們都是從維爾紐斯大學開始他們的職業生涯。雖然維爾紐斯現為陶宛的首都,但是兩次大戰之間它是波蘭的領土,維爾紐斯大學於 1922年設立了理論物理學教席,第一任講座教授是來自克拉科夫的揚·魏森霍夫(1889-1967)。魏森霍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就到瑞士的蘇黎世大學深造。 1916年,他以題為《量子理論在旋轉物體中的應用及順磁性理論》的理論論文獲得博士學位。獲得博士學位後,他繼續在蘇黎世從事實驗物理學研究一直到1919年。1919年秋,魏森霍夫返回波蘭,在克拉科夫的雅蓋隆大學物理系康斯坦蒂·扎克熱夫斯基教授的指導下擔任實驗物理助理。他後來改作理論物理,1922年至1935年,他在維爾紐斯的斯特凡·巴托里大學擔任理論物理學副教授。當時,他致力於相對論的研究,對量子理論著力不深,反而是1933年至1935年在維爾紐斯擔任助教的揚‧布拉頓(Jan Antoni Blaton 1907 - 1948 )比較活躍。揚‧布拉頓在1929年時曾擔任過魯賓諾維奇的助手,但不久便因參與左翼運動而入獄,還被大學開除。出獄後他在1931年獲得碩士學位;1932年憑藉一篇關於四極線附近光色散的論文獲得博士學位。畢業之後,他獲得國家文化基金會獎學金而前往慕尼黑,師從索末菲,繼續深造,納粹在慕尼黑發起政變後,左傾的布拉頓馬上移居蘇黎世。1933年他來到維爾紐斯的斯特凡·巴托里大學理論物理系擔任助教。布拉頓與亨里克·涅沃德尼察斯基教授在1933年共同發現了磁偶極線。 1934年,他獲得維爾紐斯大學理論物理學特許任教資格。 1935年,他發表了一篇關於四元數、半向量和旋量的論文。但他激進的左翼政治觀點阻礙了他進一步的學術生涯。1936 年,他成為華沙國家氣象研究所所長,並一直擔任該職位至 1939 年。不過由於布拉頓在華沙大學擁有副教授的資格,所以他往返於華沙與維爾紐斯授課。他在那裡開設的量子力學課程是當時波蘭最早的這類課程之一。
至於魏森霍夫則是在1935年8月回到故鄉克拉科夫的雅蓋隆大學擔任教授,從1937年起他又開始研究相對論性自旋粒子的性質。身為波蘭物理學會克拉科夫分會主席,他組織了第一次全國性理論物理研討會(1939年3月20日至22日)。1939年9月二戰爆發後他來到利維夫,並在利維夫理工大學教授實驗物理(1939年至1941年),同時繼續研究相對論自旋粒子理論。 1941年夏,他與年輕的華沙理論物理學家安東尼·拉貝(Antoni Raabe)一同返回克拉科夫。幾週後,魏森霍夫與拉貝秘密組織了一場關於相對論性自旋粒子的研討會,進行了自旋流體和自旋粒子理論的研究。拉貝後來不幸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被殺害,他們的研究成果於1946年以信件的形式發表在《自然》和《波蘭物理學報》上。
在波蘭遭到德國佔領期間,魏森霍夫參與了秘密的大學教學活動,講授實驗物理學,考核戰前秘密完成理論物理學學習的學生,並參與碩士和博士考試委員會的工作。而布拉頓則是躲在耶蓋爾森林區,並在華沙參與秘密教學。 1944年10月,他參與創建了盧布林的瑪麗亞·居禮斯科沃多夫斯卡大學,並擔任普通物理學教席。 二戰結束後魏森霍夫積極參與克拉科夫物理學的復興與發展。 布拉頓也在雅蓋隆大學擔任教授。 1947年秋季起,布拉頓在哥本哈根的尼爾斯波爾研究所工作。可惜他於1948年在塔特拉山脈登山,卻因因山難去世,齎志而歿。另一方面魏森霍夫在1947年恢復了《波蘭物理學報》(Acta Physica Polonica)的出版,並擔任該雜誌主編直至去世。 1960年至1972年,他也擔任《物理學進展》(Postępy Fizyki)的編輯。 1948年3月至9月,魏森霍夫曾在蘇黎世工業大學理論物理研究所擔任研究員,該研究所由包立領導。在那裡,他與之前的學生耶日·雷斯基以及包立周圍的一群理論學家合作,研究量子場論中的重整化和正則化問題。 所以克拉科夫與華沙,一南一北,就此成為波蘭物理界的兩大重鎮。
從量子力學引入波蘭的過程,可以看到一頁波蘭的滄桑史,許多城市在短短幾十年間多次易主,可以想見這是何等的亂世。在如此動盪的大時代中,學者們仍然努力傳襲物理的香火,實在令人萬分敬佩呀 。
另一個在兩次大戰之間動盪不安的國家則是波蘭東邊的超級大國:蘇聯。在第一次大戰爆發前,德國,奧匈帝國境內有許多來自俄羅斯帝國的年輕學子,但是隨著第一次大戰爆發,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內戰相繼爆發,新成立的蘇聯與歐洲的學術交流在一戰剛結束的時候,幾乎全部停擺。所以量子力學傳進蘇聯靠的是極少數有幸在歐洲訪問的蘇聯學者。其中最重要的是雅可夫‧伊里奇‧弗倫克爾(J. Frenkel,1894-1952)以及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德羅維奇·福克(Vladimir Aleksandrovich Fock,1898 –1974)。我們先介紹這兩位。
雅可夫‧弗倫克爾於1894年2月10日出生於俄羅斯帝國頓河畔羅斯托夫的猶太家庭。1913年冬季學期他被聖彼得堡大學錄取。他只花了三年時間就從大學畢業,並留校準備擔任教授。由於十月革命的事件,他的碩士學位口試被推遲了。由於母親健康狀況惡化,他的家人搬到了克里米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後幾年以及1921年之前,弗倫克爾與伊戈爾·塔姆一起)參與了克里米亞大學的創建。之後弗倫克爾回到聖彼得堡,終生都在列寧格勒物理技術研究所工作。(聖彼得堡於1924年更名為列寧格勒)
從1922年開始,弗倫克爾幾乎每年都會出版一本書。 1924年,他發表了16篇論文,其中5篇基本上是他其他俄文出版物的德文譯本、三本書,並編輯了多部譯本。 他是蘇聯第一部理論課程的作者。他的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電動力學、統計力學和相對論,但他很快就轉向了量子理論。他在列寧格勒的一次會議上認識了萊頓的教授,保羅·埃倫費斯特,後者鼓勵他出國進行合作研究。 所以在1925年至1926年間,弗倫克爾到德國訪問,大部分時間在漢堡和哥廷根。也就在這段時期,薛丁格發表了關於波動力學的開創性論文,弗倫克爾很快就熱情地投身於這一領域。據說他與克萊因幾乎同時發現了克萊因-戈登方程式。
回到蘇聯後,弗倫克爾持續研究工作,在研究凝態分子理論(1926年)的過程中,弗倫克爾引入了晶體空穴的概念,在1930年代,他的研究補充了塑性變形理論的工作。他的理論,現在被稱為弗倫克爾-康托羅娃模型,塔季揚娜‧康托羅娃是弗倫克爾的博士生。激子的概念最早就是由弗倫克爾於1931年提出,用於解釋絕緣體中的原子激發。他指出激發態可以像實體粒子一樣在晶格中穿行而不發生電荷轉移。但是當時並不是一個學者能夠安心做學問的時代。史達林在在1930年代掀起史無前例,極為殘酷暴虐的「大整肅」,沒有人能置身事外。弗倫克爾和老一輩的實驗物理學家約費(Abram Fedorovich Ioffe 1880–1960) 以非凡的勇氣力挽狂瀾,反對蘇聯物理學中將自然科學與唯物主義意識形態捆綁在一起的危險傾向。由於他們的努力,蘇聯物理學才沒有像生物學那樣墮落到深淵。儘管如此,弗倫克爾後來不得不放棄發表幾篇論文,因為他擔心這可能會帶來嚴重的後果。弗倫克爾於1952年在列寧格勒去世。他的兒子維克多·弗倫克爾撰寫了其父雅科夫·伊里奇·弗倫克爾的傳記:《他的工作、生活和書信》。
另一位將量子力學引進蘇聯的是福克(Vladimir Aleksandrovich Fock,1898 –1974)。他也是在聖彼得堡求學,但高中畢業前,第一次世界大戰於1914年爆發。當時聖彼得堡更名為彼得格勒,因此福克於1916年高中畢業後進入彼得格勒大學物理與數學系學習。大學入學不久,福克志願參軍,並接受了短期砲兵訓練,隨後被派往前線擔任砲兵軍官。他運氣很好,沒死在戰場上,1918年退伍後,回到彼得格勒大學繼續學業。對福克而言,這無疑是一段充滿戲劇性的時期。不僅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了俄羅斯經濟上的毀滅性打擊,而且到1918年,俄國還深陷於始於1917年的俄國革命後的內戰之中。福克很幸運,彼得格勒在1919年新建了一所國立光學研究所,組成了一個特殊的學生小組,旨在確保最優秀的學生,即使在國家局勢混亂的情況下也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福克被選中成這個特殊小組的成員,而且名列前茅,令人刮目相看。他在1922年從彼得格勒大學畢業之前,就已經發表了兩篇論文,一篇是關於量子理論的,一篇是關於數學物理。畢業後,他繼續留在大學從事研究。但是當時人在蘇聯的福克並沒有辦法追上在西歐正如火如荼展開的量子物理急速的發展。
這一切都隨著波動力學的問世而有所改變。當薛丁格於1926年春季發表了兩篇關於波動力學的奠基性論文時,福克與弗倫克爾一樣大為興奮,隨即著手發展這些思想,並在同年年底發表了兩篇關於薛丁格方程式的重要論文。這使得他的工作重要性得到了廣泛認可,也因此獲得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得以在哥廷根和巴黎學習一年。他在1928年發表了一篇關於狄拉克分佈理論的重要論文。回到蘇聯後,他開始傳授新物理給新世代的學生, 1932年,福克與波多爾斯基和狄拉克共同發表了一篇關於量子電動力學的重要論文,其中引入了多重時間公式的概念。同年,福克在另一篇經典論文中提出了福克空間的概念。就在這一年他被任命為列寧格勒大學理論物理學教授。
福克很快成為蘇聯量子理論的大師。他的名字與許多概念和成果連結在一起。像是福克空間;福克真空;福克量化方法;福克固有時間方法;哈特里-福克方法;福克對稱性;克萊因-福克-戈登方程式;福克-克雷洛夫定理;以及狄拉克-福克-波多爾斯基形式體系,這恰恰反映了他的學術成就。儘管福克取得了巨大的科學成就,但1930年代對他來說卻仍然是極為艱難的時期。 他在1930年代未能倖免於(所幸是短暫的)逮捕。他毫不畏懼地為那些被非法逮捕的同事辯護,並積極對抗蘇聯時期針對物理學的意識形態攻擊。然而,不是每個人都能幸運地從虎口逃生,即使是物理天才也無法倖免。像福克的學生,馬特維·彼得羅維奇·布朗斯坦(Matvei Petrovich Bronstein ,1906 –1938) 就死得不明不白。他是一位醫生的兒子,擁有猶太血統。1926年至1932年在列寧格勒大學求學,之後在列寧格勒物理技術研究所工作,當時弗倫克爾和約費是該研究所的負責人。布朗斯坦被認為是當時最有前途的青年理論物理學家之一,與他齊名的還有列夫·藍道、喬治·伽莫夫、維克托·安巴爾楚米揚(Viktor Amazaspovich Ambartsumian,1908-1996)和德米特里·伊凡年科(Dmitri Dmitrievich Ivanenko 1904 –1994) 。他在研究所任教,撰寫評論文章,並發表了大量科普文章。1930年代,布朗斯坦從事物理學多個分支領域的研究,包括半導體理論、量子電動力學、天文物理學和宇宙學。他關於半導體物理學的綜述文章影響深遠,當時半導體物理學是列寧格勒物理研究所的新興研究領域。然而,他拒絕了弗倫克爾1934年授予他俄羅斯博士學位的提議。他也教授核子物理學,這是該研究所的第二大研究方向,並從1932年起被分配到約費和庫爾恰托夫負責的相關研究小組。儘管他在核物理學方面發表的論文不多,但他致力於該領域在天文物理學方面的應用,例如宇宙射線和超新星爆發的起源。他才華洋溢,絕對不輸給後來大放異彩的其他同學。1932年,布朗斯坦與伊凡年科合作,將狄拉克的量子力學經典教科書:量子力學的原則,翻譯成俄文,並於1937年出版。他同時是最早研究量子重力問題的學者之一。與馬庫斯·菲爾茨、包立和萊昂·羅森菲爾德一樣,布朗斯坦認識到,對應於廣義相對論的線性化重力場理論等價於自旋為2的量子場理論。然而,他預見到由於理論的非線性特性,量子化將面臨許多困難,並推測最終可能需要一個全新的時空概念。這樣的英才卻遇到一場劫難,當時蘇聯正開展一場反對現代物理學的運動,甚至一度剝奪了伊戈爾·塔姆和列昂尼德·曼德爾施塔姆等著名理論物理學家的教學資格。當埃德溫·哈伯發現的星系紅移現象的解釋。蘇聯當局沒有將其歸因於宇宙膨脹,而是聲稱這是光子老化(衰變)造成的——布朗斯坦駁斥了這個理論。或許這就是帶給他殺身之禍的主因。 1937年8月,布朗斯坦住在聖彼得堡魯賓斯坦街38號的公寓裡遭到逮捕,在大整肅期間,他的雙腿還被獄卒打斷。1938年2月,他被審判定罪,並於當日在列寧格勒內務人民委員會監獄的地下室被處決。他被捕的確切原因至今不明,實在令人扼腕。
相形之下,大難不死的藍道後來能夠在物理世界大放異彩,就實在是太幸運了。1924年,藍道進入列寧格勒國立大學。在這兒他第一次認識到真正的理論物理,並且決定全心投入這方面的研究。藍道在列寧格勒大學時常與喬治·伽莫夫和德米特里·伊凡年科交流物理前沿的學習心得,這3人被稱為該校的新銳少年「三劍客」。也有人把布朗施坦因也算進去。1926年,藍道發表第1篇關於雙原子分子光譜譜線理論的論文。1927年從該校畢業後,他進入列寧格勒物理技術研究院,並在1929年(21歲)取得副博士學位。不過由於當時學術環境相當混亂,藍道並沒有寫出正式的畢業論文就拿到了學位。同年,在蘇聯政府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下,藍道到歐洲各地學習。他先是在哥廷根和海森堡剛搬過去的萊比錫短暫地停留,接著來到哥本哈根理論物理研究所,跟從著名物理學家波爾等人研究量子力學。後來藍道時常自稱自己是波爾的學生,雖然他只在波爾研究所工作了4個月而已,藍道參加了波爾主持的理論物理討論班,初步展露出他驚人的才華。據說愛因斯坦有一次在那裡演講時被年輕的藍道敏銳地指出了一處推理漏洞,轉而對著黑板思索後說:「後面那位年輕人說得完全正確,諸位可以把我今天講的完全忘掉。」
離開哥本哈根之後,藍道還訪問了劍橋和蘇黎世。當時在瑞士蘇黎世讀博士後的派爾斯(Rudolph Peierls)回憶說:「我還清晰記得藍道1929年在蘇黎世出現在包立的系裡時,給我們留下的深刻印象。 ...沒過多久就能發現他對現代物理學的深刻認識和他解決基礎問題的技巧。他很少詳細閱讀理論物理學的論文,只是大概看看問題是否有趣,如果有趣,作者的方法是什麼。然後他開始自己計算,如果答案和作者的一致,他就贊同這篇文章。」他在劍橋時,參訪了拉塞福主持的卡文迪希實驗室,並在那裡結識了另一位蘇聯物理學家彼得·卡皮察。 這個幸運的邂逅日後救了藍道一命!
藍道於1931年回到蘇聯。不久後,蘇聯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急速惡化,藍道此後再也無法前往西方國家交流。1932年-1937年,他擔任哈爾科夫物理技術研究所的理論部主任,1937年,藍道前往莫斯科,在卡皮察的物理問題研究所擔任理論部主任。 未幾,在大整肅期間,藍道在寫給他的朋友摩西·科列茨在信中譴責史達林,甚至把史達林政權與納粹德國和義大利法西斯政權等同,甚至打算號召推翻史達林主義政權。二人原計劃在五一勞動節散發該傳單。不意外地藍道和科列茨等友人因「煽動反革命罪」在1938年4月28日被捕,藍道被關押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監獄。為了把藍道保出來,彼得·卡皮察私底下寫信給史達林擔保藍道的行事作為,並親赴克里姆林宮為藍道說情。卡皮察擔保全蘇聯只有藍道才有能力解決自己一年前在實驗中所發現的液氦超流態的物理機制問題,從而為蘇聯在國際上爭光。幸運的是,頭號特務頭子貝利亞居然相信了卡皮察。在卡皮察等人的努力下,藍道一年後獲釋。他也不負眾望,成功建立了液氦超流性的理論。 後來更成為蘇聯物理界毋庸置疑的領頭羊。他的成就勝過弗倫克爾,福克與下場悲慘的布朗斯坦,但是他們三人將量子力學引進蘇聯的功勞還是不能抹煞。冷戰時代的蘇聯變成物理大國,不能不歸功於他們的努力。
我們從上述這幾個國家學習量子力學的過程可以看到哥廷根的波恩,慕尼黑的索末菲扮演著吃重的角色,日本科學家湯川秀樹曾經轉述過當年波恩即使拖著疲憊的身心,也要在家中款待外國的留學生,並且熱心地與他們討論物理。我們可以看到物理香火的傳承,是建立在許多人無私的奉獻上,你是否覺得很不可思議呢? 下一回我們要繼續介紹量子力學是如何傳播到義大利,甚至亞洲與南美洲,請不要錯過!

